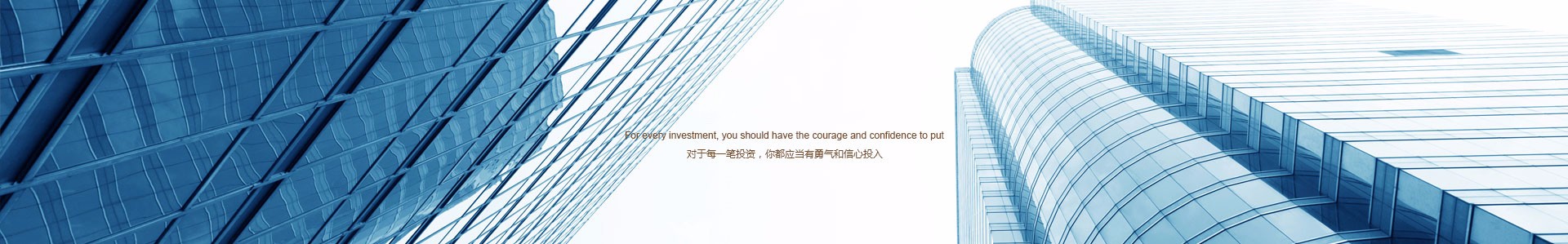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基金161601棋牌游戏- 棋牌游戏平台- APP下载)
2025-10-07棋牌游戏大全,棋牌游戏app,棋牌游戏平台,棋牌游戏赌博,棋牌娱乐,棋牌娱乐平台,棋牌论坛,棋牌,开元棋牌,棋牌游戏有哪些,斗地主,扑克游戏,麻将,德州扑克,牛牛,麻将糊了,掼蛋,炸金花,掼蛋技巧,掼蛋口诀,抢庄牛牛,十点半,龙虎斗,21点,贵阳捉鸡麻将,牌九

睡眠医学是一门综合性强且发展快速的新兴交叉学科,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睡眠与觉醒、昼夜节律的生物学机制、各类睡眠障碍的病理生理机制及临床诊疗等[1]。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各种睡眠障碍逐渐成为突出的医疗及公共卫生问题[2],这对睡眠医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国家科技计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增强源头创新能力[3],对推动睡眠研究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利用1988—2019年睡眠研究领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资料,系统回顾睡眠研究的发展情况及变化趋势,展望睡眠医学未来发展,以期为睡眠研究领域的政策决策者、科研工作者和管理者提供参考。
1988—2019年睡眠研究领域共立项399项,共包括8种项目类型,分布在医学科学部和生命科学部的21个一级代码、64个二级代码下。1988年之一项有关睡眠疾病的研究立项,但1990—2001年该领域立项项目为空白。2002年后该研究领域每年有立项项目,从2002年的4项增加到2019年的51项。从变化趋势来看,立项总数整体呈增长趋势,特别是2010年以后立项数量增长明显;立项总数从1988—2009年的46项增加为2010—2019年的353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以下简称面上项目)从29项增加为166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从14项增加为125项。面上项目占比从1988—2009年的63%下降至2010—2019年的47%,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占比从30.4%增加至35.4%,见图1。在项目类别构成方面,以面上项目(195项,占48.87%)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39项,占34.84%)为主,地区科学基金项目38项(占9.52%),重点项目4项(占1.00%),其他项目包括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应急管理项目、专项基金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占5.77%);但1988—2019年重大研究计划及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等重要人才类项目未立项,见图2。
1988—2019年,睡眠研究领域所有项目资助总金额为16 410.05万元,以面上项目为主(共9 798万元,占59.71%),其次为青年科学基金(共2 846万元,占17.34%)。从变化趋势来看,各类别项目资助金额整体呈增长趋势,特别是2010年以后资助金额增长明显;总资助金额从1988—2009年的1 076万元增加为2010—2019年的15 334.05万元,其中面上项目资助金额从619万元增加为9 179万元,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金额从284万元增加为2 562万元,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应急管理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资助从无到有,资助金额分别为1 528万元、70万元、218万元。各类型项目的资助金额及历年资助金额变化情况详见表1和图3。
1988—2009年6个地区共13个省(市)受到项目资助,而2010—2019年项目资助覆盖全国,除海南省及港澳台等地区外,其余30个省(市、自治区)均得到项目资助。从地域分布来看,1988—2009年华北地区的立项数量和资助金额排序之一,华东地区排序第二;2010—2019年华东地区的立项数量和资助金额排序之一,华北地区排序第二;比较1988—2009年和2010—2019年立项情况,华中地区排序上升至第四位,华南地区排序由第三位下降至第六位,东北地区排序由第五位下降至第七位。在变异程度上,1988—2009年地域之间立项数量为(9.00±6.56)项,变异系数为0.728 6;资助金额为(210.00±188.56)万元,变异系数为0.897 9;2010—2019年地域之间立项数量为(50.43±37.86)项,变异系数为0.750 7;资助金额为(2 190.58±1 757.46)万元,变异系数为0.802 3。从省域分布来看,1988—2009年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位于立项数量、资助金额的前3位,立项数量和资助金额在全国的占比均超过10%;2010—2019年北京市、上海市和江苏省位于立项数量、资助金额的前3位;比较1988—2009年和2010—2019年立项情况,上海市有上升趋势,北京市有下降趋势,江苏省上升明显; *** 自治区、青海省、宁夏 *** 自治区在1988—2009年无立项项目,2010—2019年的立项数量排序靠后(排序分别为第30、29、28位),且在2019年度也无立项项目,见表2。
按照公式2分别计算1988—2009年和2010—2019年各机构的竞争力指数结果,详见表3,表4。1988—2009年获批睡眠研究领域项目的依托单位共27个,其中18个机构分别立项1个项目,其他9个机构的立项数量为2项或以上;竞争力指数排序前3位的分别是北京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天津医科大学;立项数量前10位的单位合计项目数占全国的63.04%;资助金额前10位的单位,合计资助金额占全国的68.20%。2010—2019年获批睡眠研究领域项目的依托单位共94个,其中41个机构分别立项1个项目,其他53个机构的立项数量为2项或以上;竞争力指数排序前3位的分别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立项数量前10位的单位合计项目数占全国的43.91%;资助金额前10位的单位,合计资助金额占全国的48.31%。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睡眠障碍认识的不断深入,我国在睡眠研究领域不断突破。研究可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数量从1988年的1项增加到2019年的51项,资助金额从1988年的1.5万元增加到2019年的1 987万元,均有了巨大飞跃;项目类型逐渐丰富,每年立项从最初的只有面上项目增加为最多7种项目类型;立项项目的依托单位显著扩大,依托单位数从1988—2009年的27个增加至2010—2019年的94个;立项项目的省域分布极大地扩展,从1988—2009年的13个省(市、自治区)增加至2010—2019年的30个。以上说明国家对于睡眠研究领域的投入和支持力度明显加大,整体科研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2009年9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成立,加强了战略引导,加大了健康领域资助力度[5],专门设立睡眠呼吸障碍(代码为H0113)和睡眠与睡眠障碍(代码为H0916)资助睡眠研究。从2010年开始睡眠医学领域立项数量与资助金额增加明显,并且立项了重点项目支持睡眠医学领域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6],极大地促进了睡眠研究的发展。
1988—2019年睡眠研究领域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等重要人才类项目未立项,重大研究计划也未立项,说明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对睡眠研究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国家对该领域科研的财政支持还需进一步加强。睡眠研究领域立项项目分布在医学科学部和生命科学部的多个代码下,较为分散,尚未形成研究合力,体现了睡眠领域科研竞争力和系统性的不足,我国的睡眠研究整体尚处于初级阶段。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则高度重视睡眠研究,美国在国立卫生院的心肺血液病研究所中成立国家睡眠研究中心,分别于1996年、2003年、2010年、2021年发表国家睡眠研究战略计划,指导睡眠研究的发展方向[7]。因此,我国仍需从顶层设计和宏观布局不断提高睡眠研究水平这一持久驱动力,增加指南引导类项目及有组织的科研,以支撑学科快速发展。
睡眠研究领域立项项目的数量和资助金额在省域及地域分布存在明显不均衡性。从省域分布来看,2010—2019年,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成为睡眠研究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的聚集中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实力相匹配。从地域分布来看,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的立项数量和资助金额始终处于前两位,这两个地区也是医学院校、医学科研机构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随着睡眠研究领域科研整体实力的提高,产生了聚集趋势和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在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配中普遍存在,其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8],聚集趋势和马太效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在睡眠研究领域科研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将基金更多地分配给科研能力和科研需求强的团队,可以有效促进科研效率提升。同时看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成立之后,通过地区科学基金形式帮助 *** 、新疆等地区实现了睡眠研究领域资助的突破,发挥了高原环境等独特地理优势,推动了西部欠发达地区睡眠研究的进步。此外,对于青年科学基金等可以给予政策支持,增强睡眠研究的后备力量,培养更多从事睡眠研究的优秀青年学者,使得我国睡眠医学发展更科学、更健康、更有活力。
高等院校(含附属医院)是睡眠研究的主体,从1988—2009年到2010—2019年,竞争力指数排序前3位的单位从综合院校和医学院校并重转变为全部是综合院校,符合睡眠医学交叉学科的特点,也体现出综合院校在交叉学科研究中的优势。2010—2019年竞争力指数排序前3位的单位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其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生物学专业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均为A-及以上[9],说明睡眠医学等学科的发展需要依托良好的传统基础学科的实力。例如,北京大学成立的睡眠研究中心[10]整合了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生物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等多学科力量,发挥竞争优势,同时通过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发挥北京大学龙头引领作用,有效推动了睡眠医学研究水平。睡眠研究必须依靠学科交叉融合,以解决睡眠障碍为目标,组建科技攻关团队,促进我国睡眠研究水平不断提升。
睡眠医学涉及多个学科,除了呼吸、神经、精神、心理、耳鼻喉科、口腔科等专业外,还需要全科医师的广泛参与,通过开展睡眠呼吸暂停的家庭无创通气治疗为其他慢性疾病家庭医疗的开展提供借鉴[11],借此逐步探索新型家庭医疗模式。采用睡眠医学+模式[12],允许完成呼吸、神内、耳鼻喉、精神等培训的专业医师参加睡眠医学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更系统、规范地培养睡眠医学专业人才是推进睡眠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途径。
目前睡眠研究领域仍有许多未知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睡眠觉醒、节律转换与维持的神经机制,睡眠觉醒、节律调控的分子机制,基于睡眠认知功能的调节 *** ,延缓睡眠功能减退或者睡眠紊乱的普适性 *** ,睡眠障碍新型干预治疗手段,睡眠调控技术对代谢、免疫功能的影响等。在未来的睡眠研究中,需要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睡眠-觉醒的发生机制和功能,结合分子遗传学、表观遗传学、多模态成像等技术,进而实现睡眠障碍的早期预防和诊疗干预精准化。
前光大证券分析师刘均伟曾指出,“爆款”基金是牛市下的产物,而牛市是把双刃剑,可以让踩准节奏的基金产品成为爆款,但后续业绩表现若不尽人意,不仅规模缩水,也将对投资者带来伤害。“爆款”基金后续份额的变化主要受业绩主导,据其统计历年年末规模排名前十的主动权益类基金数据,大多数基金是依靠首发优势进入前十,且依靠首发规模进入前十的主动权益基金,若后续业绩表现一般则规模将出现大幅下行。首发规模过高的基金往往在管理难度以及基金经理心理压力上均较大,若业绩表现一般,将面临大量赎回,对投资者而言造成的伤害极大,也不利于基金公司对客户的维护。
一是完善科学基金项目科技伦理行为规范。坚持确立细则化、系统化标准体系,在科技共同体中形成良好的集体行为习惯,为科技创新提供正向的、良性的引导,是科技伦理规范体系建设的核心构成部分。基金管理机构在规范建设中应坚持底线原则。科技伦理规范只是为科技行为的治理提供“底线”式基准,科技行为主体在合规或自律中,可以遵循更高标准,但绝对不能低于基准行事。这一原则既体现在积极的科技行为实践标准的确立和遵循方面,也应当体现在科研责任制度方面。
三是加强科学基金项目相关主体的科技伦理教育培训。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及其科研人员的伦理培训和教育至关重要。完善依托单位高等教育科技伦理课程内容设置,强化教育的组织和设计,不能简单依靠科学共同体的自为与自组织,科学基金资助机构须担当较多的主导和组织性角色。加强科学基金项目的科技伦理教材与教学内容建设,在全方位比较分析各国、各地区科技伦理政策法规异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和制度环境、文化特征来组织教材和教学内容的编写。
四是坚决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部门关于科技伦理的治理政策。《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印发后,各科技管理部门也将结合分工制定落实的相关政策文件,科学基金须按照有关政策文件要求对科学基金项目违反科技伦理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惩处,包括取消资助项目、收回资助项目资金、取消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若干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等,对违反科技伦理的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形成震慑,让科学基金项目在科技伦理的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切实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基蓄势,提供坚强科学基础。